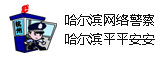刘风孩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把这一生的秘密都带进黄土,不再叫别人知晓。(张亚运/图)
郭柯最初也曾戴着有色眼镜,抱着猎奇的心态去看待慰安妇群体。他想直达她们心底最深的地方:“这样的女性,当时受过那么大的伤害,现在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就想去一窥究竟。”如今郭柯却觉得,“老人不想说了,我们为什么要逼她们说呢?”
志愿者张双兵现在想想,当年带着这些老人到日本去,让日本政府给她们赔钱和道歉,“可是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
2016年8月初的一个午后,在山西沁州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只躺着骈焕英一个人。病房的窗户开着,从窗口飞进来的苍蝇在她上方盘旋,有几只甚至落在了她的衣服上。
90年的岁月,在骈焕英的脸上镌刻成一道道皱纹和稀疏疏的斑点。她呼吸得很费力,从她胸腔里发出颤颤巍巍的粗气,像奄奄的火种将灭将息。此时,房间里响起黑色单反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一些外来探望者的声音惊动了她。骈焕英微微张开眼睛,愣了一会儿,慢慢地挥起手说,“走吧,走吧。”随后又闭上了双眼。
骈焕英是一名慰安妇。七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期间,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亚洲女性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并伴随监禁和暴行。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中国有逾20万慰安妇。然而现在,全国已知的受害者却仅剩20人了。
这些老人主要分布在山西、海南、广西、湖北、湖南五省份,其中山西省最多有9人,海南有7人,湖北2人,湖南和广西各有一人。她们平均年龄都在90岁上下,基本上疾病缠身,行动不便。
20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并不宁静,形形色色的人围绕着她们:志愿者,学者,公益人士,作家,导演等等。他们有的的确出于同情向她们捐助金钱,也有人出于民族大义研究属于她们的那段历史,有人则完全出于功利目的来消费她们经历的苦难。
8月14日是世界第四个“慰安妇日”,今年恰逢世界各国联合将慰安妇资料申请世界记忆名录。中国大陆各地抗战史专家和民众,云集亚洲慰安妇最大的纪念场所——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
毋庸置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那段历史,然而中国仅存的这20个老人,也已经进入到她们人生的晚年岁月。
败兴
很少有人知道,作为一名慰安妇到底要遭多少罪,就连骈焕英自己也很难表述得清。
1942年秋天,山西沁县暖泉村,在那个抗日正酣的年代,14岁的骈焕英先后4次被日军抓进据点。 “一提起当年,她就说身上觉得凉哇哇的,牙齿就胡散(指因害怕嗦嗦嗦嗦地抖)开了。”骈焕英的小儿媳说。
根据《沁县县志》记载,1939年至1945年,该县因被日军强奸而患性病、精神失常、肢体残疾的妇女多达1641人。
慰安妇的经历会留下一辈子的痛。按照海南志愿者陈厚志的形容,幸存的受害者们,毛病从头到脚都有,精神上还带有以前战争留下来的记忆。另一位海南志愿者透露,“当地一位已经离世的慰安妇生前一直有个习惯,睡觉时会拿一把柴刀放在床边。”
对那段日子有着噩梦般回忆的还有李爱连。1946年,山西武乡县邵渠村的李爱连曾两次被抓到附近的南沟据点,日本人关了她27天。当时,日本人的部队和番号还一直占领着南沟,继续糟蹋着女人。日本兵在武乡县故城镇范围内总共逮捕了380人,其中一百多人是女人。“(日本人)用棍子打我们,每个人还被点名。”李爱连回忆说。
她看见民兵和日本人打仗,日本兵用刺刀对着民兵的肚子“刺刺刺”,“头上、身上到处都是血,我都不敢看。后来收尸的时候,骨头都是碎的。”
逃跑回家之后,李爱连久久说不出话来。母亲问她怎么了,她哭着说:“我回是回来了,后面还有人呢。”母亲又问:“你二哥呢?”她说:“俺二哥死了(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母女俩就抱在一起哇哇地哭。
17岁时,李爱连有了第一个老汉,三十多岁的时候,第一位老汉不在了。后来,她在县城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家在晋城高平市的老汉,又结婚了,生了现在几个儿子。十几年前,第二个老汉也离开了人世。
李爱连总说丈夫没有嫌弃她,但终归还是觉得她败兴(指丢人)了。无论怎样,慰安妇的经历还是给她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慰安妇纪录片《三十二》的导演郭柯和她相处了整整7天,才慢慢打开了她的话匣子。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慰安妇和劳工伤害、大屠杀不一样,这是性伤害,对中国女性来说这是最难以启齿的事情。”
有慰安妇的村子经常遇到这样一幕:当外来者的车辆又开进村子时,坐在村口闲聊的人们就开始互相交流着眼神,他们心知肚明,“又有人给她家送东西了”。更有甚者,大半个村的男人都会挤在受害者的院子里看热闹。
“村里人会说三道四,每说一次,以前的事就会被翻出来一次。村里的人说话也不像城里那么含蓄,很直白,有时候也不好听。”导演郭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为了躲避流言蜚语,沁县另外一位做过慰安妇的老人一直被在教育局工作的儿子藏在家中,不让外面来的人看她。
现在村里人常对李爱连说,“那么多人给你送钱呢,你老婆婆不缺钱呀。”这么多年的风言风语听惯了,她倒是无所谓:“哎,送了一点点钱,别人还以为送了好多,说就说吧。”
疏离
骈焕英从来不跟儿女提起那些糟心的事。在老幺(指最小的孩子)田五平模糊的童年记忆中,只有一次,母亲和亲戚拉家常时提起:“日本人把她拉到一个炮楼还是什么地方,不让回来,做了坏事。”
再往后母亲就不说了,可她却还留下一句清晰的话:“小日本可坏了!”尤其是在看到电视里有日本人欺负人、杀人的时候,骈焕英常常说类似的话。
当地资深慰安妇民间调查者、山西盂县羊泉村村民张双兵发现,“(这些慰安妇)最忌讳跟子女说当年的事儿,互相都当不知道。有些人终身都被毁了,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有儿女的也会受到牵连,他们找不到对象。”
似乎是一种默契,骈焕英的子女们都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下一代人,“让孩子们知道了,说不定一辈子也是个结。”除了大孙女隐晦地知道一点以外,在外读硕士的二孙子也只是以为“外人是来向奶奶了解日本人在的时候的历史”。
与外来者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不同,田五平并不想知道母亲那段历史。田五平承认,母亲的过去让他觉得有点儿不光彩,“好像被人戳了脊梁骨”。
“那是战争,谁也阻挡不了。”四儿子田伟平感叹说,父亲早逝,他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拉扯他们长大的苦日子,“只能吃杨树叶子,直到过年才能买八斤好面。”
骈焕英一共有五个儿子,都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每年却只相聚两三次。一次是过年,一次是骈焕英生日,再有就是家里有红白喜事的时候。
因为那段历史,老五田五平明显感觉和母亲的话越来越少,有些东西横亘在他们之间,慢慢渗入到了生活的肌理。“感觉有点淡,又有点尴尬,像中间隔着什么。”田五平坦陈,他不知道真相的时候什么都好说,一旦知道了真相却不愿意接受。
骈焕英也并非察觉不到子女心理的变化,有时候她觉得孤单了,也会生气。“有什么事她都不明说,就让你猜。比如她想吃个啥了,你猜到最好,猜不到就和你生气,夜里不睡觉。”田伟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日子
骈焕英几个儿子家家都不宽裕。老四田伟平和媳妇两人以卖菜为生,但今年因为雨水太猛,西红柿和黄瓜都长得歪瓜裂枣,卖不出去。
在儿子们眼里,母亲也不是很缺钱。虽然骈焕英不是低保户,每年只有几百块钱的农村养老保险,但她还有几块别的收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每年会资助每个受害者5000元;也有来自香港的基金会给老人们些钱;此外,韩国和日本的民间组织或团体也会捐款。
骈焕英没有自己的家,她平时在几个儿子家轮流住。大儿子年龄大了,家不仅小而且离得远,二儿子没有老婆,骈焕英也不愿去老三那里。她就在老四和老五两家轮流住,一家呆一个月。
平日里,老人们基本上哪里都去不了,她们腿脚都不好,只能呆在床上,有人来就聊天,没人来就发呆。到了饭点儿,就等子女做好饭端上来。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几位老人,发现她们普遍精神状态不错,对待来访的人也很友善,要是客人买了东西,有的老人还会客气地说“别买东西”。清徐县的郝月莲特别喜欢小孩子,只要看到年轻人到她家去,她就高兴。。
不过,也有老人对待来访者的身份比较警惕。8月2日,志愿者前去探望太原市阳曲县北温川村93岁的刘改连。可当志愿者说明来意后,刘改连坚决不让他们进屋,她杵着拐杖站在院子中央,冲着志愿者们喊:“我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哪一国的,没那么简单,不能随随便便糊弄我,叫个我认识的来!”
即便过去了几十年,一些老人提及那段令人痛苦的记忆时还是很悲愤。“恨,怎么能不恨他们(日本人),他们杀人放火,来了进门就打人,又打老婆,又打孩子,那个刺刀很可怕。”说起往事,太原市清徐县的郝月莲很激动,以致心脏不舒服得躺下了。
不知道是犯了糊涂,还是故意地回避,郝菊香说自己“从没见过日本人”。但她却能清晰地指认出报纸上印着慰安妇大头像的人们都住在哪里,“这个离这五里地,这个离这二里地。”
总体来看,老人们的日子倒也还不算难过。去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甚至有的受害者家里每个月都有人来,“来了就会多少给他们点钱”。不过,就算这种零散的票子,也总免不了有些惹麻烦。
不久前,上海高校的志愿者去取一位已故受害者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准备收入慰安妇博物馆保存。一开始,家属因为石子路不好走不愿意出来,但第二通电话里说“有100块钱的使用费”,夫妻俩就立马开着面包车颠颠簸簸地出来了。
类似的事情在慰安妇周围一直就存在。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曾经沁县有一位志愿者,每次带着外人来探望她们,自己都会要走一半的慰问金,不给就威胁她们不再带外人来了。”
“所以有时候去看她们,身体还不错的老人,我们就到外面把钱塞到她手里,还要嘱咐她无论如何要藏好。”苏智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些地方我们分月付款,尽可能请当地的调查员辛苦一点,每个月给老人两三百块钱。虽然想了很多办法,但由于我们人手、精力有限,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
这两年自告奋勇帮助苏智良送钱的导演郭柯,也积累了不少照顾老人的经验,他总结说:“有的钱能给子女,有的钱必须给老人,有的钱就得给邻居。”
反思
“我们到底为什么来拍这个,把她们的伤痛挖出来给全世界的人看?”2012年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三十二》在网上反响热烈,但片子的导演郭柯却开始反思:这部纪录片不像剧情片可以虚构,而是真真实实地发生过,“老人不想说了,我们为什么要逼她们说呢?”
他承认拍摄这个题材一开始是有功利心的,慰安妇群体有特殊的社会探讨价值,也具备话题性,可能会受到国际关注。“新导演都想自己被认可,(拍个好片子)去拿奖什么的,还是奔着这个目的。”郭柯说。
跟其他人一样,郭柯最初也曾戴着有色眼镜,抱着猎奇的心态去看待慰安妇群体。他想直达她们心底最深的地方:“这样的女性,当时受过那么大的伤害,现在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就想去一窥究竟。”如今郭柯却觉得,“从人性关怀方面来说,我们做得不好。”
他并不是第一个反思的人。早在2006年,就凭借着相同题材获得国际摄影金奖的陈庆港也曾公开表示,“有些时候我根本就不想再向她们提问了,一个后辈去问她们几十年前那么不堪的回忆,我没有办法说出口。”
反思的人中还包括一些志愿者。从1990年代至今,中国民间开展了旷日持久的对日民间索赔行动。1992年,来自山西的刘面换、侯冬娥等四位慰安妇,第一次打破了中国社会的沉默,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她们赴日演讲、上庭作证、等待审判,折腾了十几年。但是,自从2007年被日本法院终审败诉之后,慰安妇一下找不到出路,民间对慰安妇的调查受到影响。
志愿者张双兵现在想想,当年带着这些老人到日本去,希望日本政府给她们赔钱和道歉,“可是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他有点后悔。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希望从老人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张双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曾经有一位摄影家,到了老人那里就叫她摆拍,教她做脸部的动作他来拍。后来甚至有受害者家属要起诉这个摄影家,“因为有的照片实在是面目狰狞,有点丑化她们的意味”。一位家属也曾透露,“很多记者来,就直接问问题,问哭了拍照片,逮着拍。”
苏智良认为,从历史和学术角度看,对慰安妇的调查作用不小,“它揭开了日本在中国推行性奴隶制度的真相,把这个真相揭开,细节记录下来,不让它淹没。”
2014年,导演郭柯决定再拍一部纪录片《二十二》,希望将当时幸存的22位老人的生活现状记录下来。然而,此时老人们都有了抗拒情绪,只要摄制组去了老人家里,周围的人们就会想到“又是来问这个事情的”。
沁县的刘风孩老人就不愿意让他们拍自己,结果就只让摄制组拍了房子的空镜回来。刘风孩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把这一生的秘密都带进黄土,不再让别人知晓。
时隔两年,新纪录片拍摄时选取的22位老人,已经走了8位。中国慰安妇的名单正在越来越短,总数已经只有20个。她们腿脚大多不灵便,根本下不了炕,每天醒了吃,吃了睡,睡不着就倚在炕上发呆。
已经跟老人们打了多年交道的郭柯,现在感觉自己对老人们更加理解了。明年是抗日战争爆发80周年,各界也继续为此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郭柯担心,“这群老人注定又要被推到风口浪尖。”
2015年底,山西的受害者张先兔老人去世。在她的葬礼上,来自英国、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各界人士,都极富感情地作了演讲。郭柯却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希望若干年后,我们还能记住她们的名字,不止因为她们是慰安妇。”